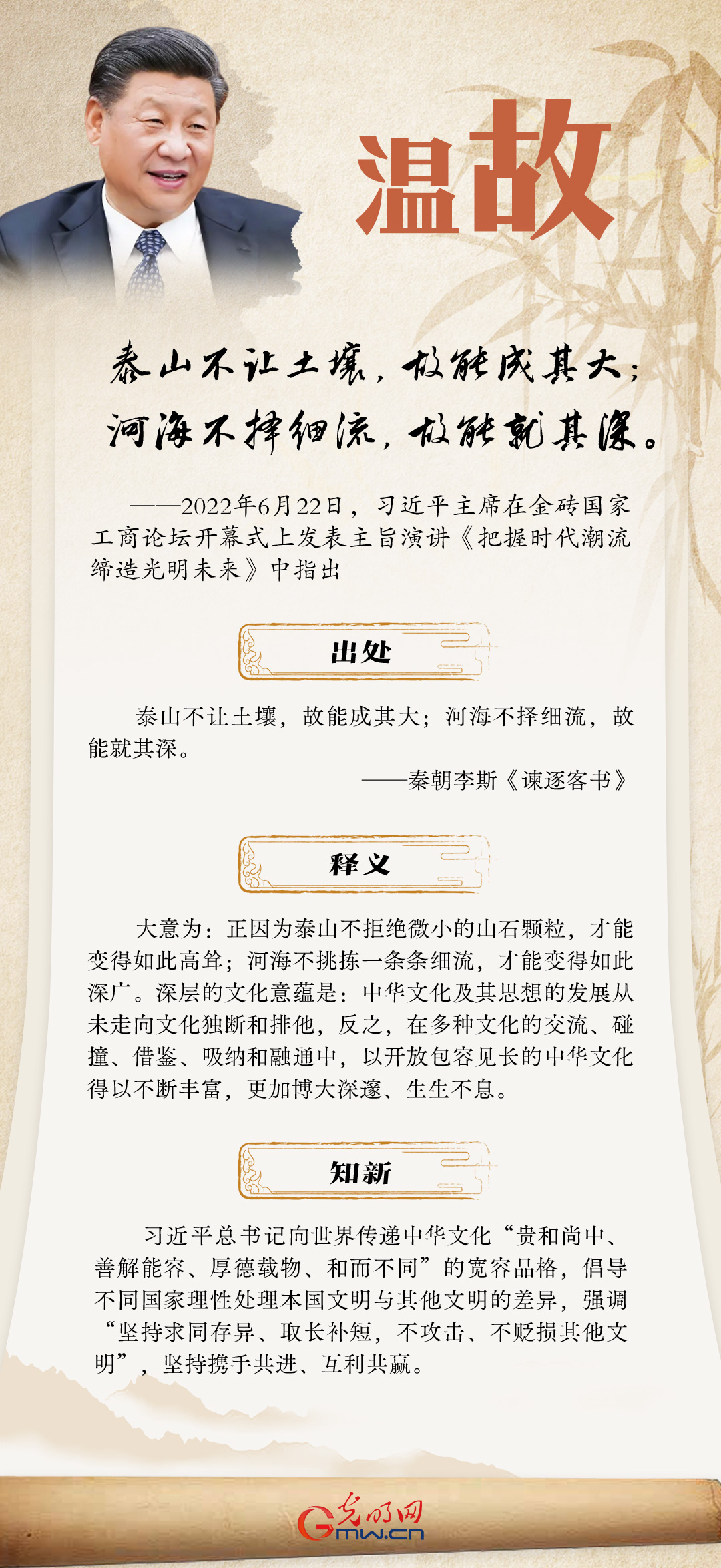中新社记者:如何从诗学“活法”引申到苏东坡的人生“活法”思考?苏东坡的“活法”究竟是怎样的“活”?苏东坡的“活法”又显现了中华文化怎样的底色?
曾明:如果将“活法”局限在文论的狭义范畴,这未免误解了“活法”。宋代之所以能一跃成为华夏文化的“造极之世”,其重要原因之一即这几乎是一个人人言活法、时时言活法、事事言活法的时代,以至于周必大在《平园续稿》中有“诚斋万事悟活法”之说。
今天,对“活法”说,我觉得应放置到更广阔的空间、更大的传统文化格局下重新审视。“活法”之“活”,既有“灵活”之意,也可以“存活”相诠,其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辩证法的实质——一个“活”字,或曰一个“变”字。然而其“活”其“变”,又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。“学古不泥古,破法不悖法。”它是中国文化智慧的精准表达。传统与现代,老树与新花,如何因“活”而“活”,是人类文化史上经久不衰的命题。
四川坊间有言:“人生缘何不快乐,只因未读苏东坡。”苏东坡不仅将“活法”贯通于诗、文、词、画、书法甚至美食之中,还将“活法”说自然而然、淋漓尽致地实践在他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快意逍遥之中。
如人们耳熟能详的,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”,其实这三州恰恰是苏东坡最失意之时,可是他却豁达地将其称为“功业”,这里流露出东坡式的自信与达观,也是我们中国人面对逆境时“潮平两岸阔,风正一帆悬”的“活法”。

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祠内的苏东坡雕像。中新社发 张忠苹 摄
苏东坡一生,在诗文上达事达理达意,在行动上达到其一生所穷尽之“理性”“得事之真”和“见物之情”。有“情”是他与其他理学家最不同的地方。
当我们穿越岁月的厚重幕幔,不难发现,苏东坡一生留下了太多的文化瑰宝,特别是他重“活法”有温度的诗文,细读检讨,常思常新。这些并不是文字的排列组合,而是流淌的岁月生命。这或许是苏东坡从宋朝走到今天,成为中华文化底色的原因。
如果我们要再进一步追问,苏东坡的“活法”究竟是怎样的“活”?那就是:以人为本,以情为本,而非以理为本,以法为本。“情”活而“理”死,“法”为“人”所创。故以法、理为本是“死法”;以人、情为本,才是“活法”。(来源:中新社 记者 贺劭清)